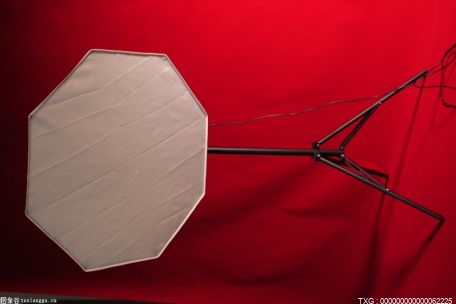江南文化最早可以溯源至史前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以及良渚文化、马桥文化等。其中良渚文化是中国最早的形态独立完整的精神文化,有着全世界最精湛的玉器、最早的大规模犁耕稻作以及中国最早的苎麻织品。如果从审美特质上对良渚文化进行描述的话,那就是血勇尚武的“外拓气象”与内敛精致的“玉质气象”并存。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上是一种集大成的文化,被考古学家认定为吴越民族的先期文化。
商末周初,吴越两国在今天的江苏、浙江、上海和安徽以及江西部分地区相继兴起。春秋晚期,句吴在姑苏,今江苏苏州建都;於越在会稽,今之浙江绍兴建都。吴乃“太伯奔吴”而建,越乃夏之苗裔,荆蛮族人所建。在吴国越国这片土地上,吴越文化逐渐定型成熟。吴越文化的最明显特征表现为对水的极度的崇拜和信仰。吴越地区,水域丰富、土壤肥沃,前阻长江、后绝大海,以水乡泽国著称。于是,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吴越之民,对水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畏惧和崇拜之情。吴国在棠浦东建祠以祭江海水神,“以利朝夕水”;越王勾践灭吴之后,“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此其时,为之立祠”。像善于治水的大禹,在吴越一直就被当治水的神灵,用来拜祭。同时,与中原地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大相径庭,吴越之地,从君王到黎民百姓,皆好“断发文身”。《春秋谷梁传》就称“吴,夷狄之国,祝发文身”。之所以如此,盖因吴越百姓“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吴越两国百姓畏惧水,崇拜水,又在水中驾舟谋生,在与水的搏斗中生存。在吴越广泛流传的大禹传说中,大禹和兴风作浪的龙神斗智斗勇,在反抗中取得胜利。在这种环境之中产生的吴越文化自然呈现出好勇开拓的文化性格。
另一方面,吴越好勇外拓的精神也在纷争的历史环境中进一步被加强。春秋至战国五百年间,周室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列国转相吞并。春秋有五霸,战国列七雄。频繁的战事和弱肉强食的局面,对当时的吴越文化产生了深刻且深远的影响。吴越两国毗邻,“同气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则越”。吴越相邻又纷争不断。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至今仍广泛流传的越王勾践二十载卧薪尝胆的故事。因为战争和北上争霸的需要,吴越两国十分重视也善于青铜铸剑,其铸造之术也远近闻名。“干越之剑,宝之至也”“古之兵器制造,以吴越为最盛”。在这种背景下,吴越文化能蕴含勇往直前、开拓图新的审美品格就在情理之中了。
战国晚期,楚怀王二十三年(前306年),楚灭越,楚文化和越文化正式融合。其实,从春秋中后期开始,楚文化和吴越文化就开始了相互交流。在吴晋抗楚,楚越抗吴,最后楚灭越这段长达一百多年的时段内,楚文化逐步向东渐进。不同于北方礼教文化的那种“质朴厚重”“刚正严肃”,特立独行的楚文化以“诡奇浪漫”“大胆浓艳”“神秘玄妙”和“任达不拘”而著称。这在楚辞楚赋中有着集中的体现。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相融之后,吴越文化开始呈现出新的面貌,其中最显著的表现就体现在,好勇尚武不再是吴越文化中最典型的存在,“尚武文化”和“重文文化”开始交汇融会。
处于江南文化初始阶段的吴越文化,此时还只是长江下游的区域文化。随着中国经济重心、文化重心和政治重心的不断南移,江南文化逐步树立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吴越区域文化开始步入“中国的”江南文化范畴。钱穆认为,“东晋南渡,长江流域遂正式代表着传统的中国”。谈玄尚韵的东晋和好药酒、重姿容、品神韵的“魏晋风度”为此时的江南文化注入了讲意境求幽远、风流恣情、澄澈重情、超然隐逸等新的特质;辞藻华丽、对仗工整的“元嘉体”,工巧华美、清新通畅的“永明体”,清秀拔俗的“吴均体”也为诗坛树立了新的美学风范;南朝清新活泼的江南民歌,既大胆热烈又执着朴素,有着美好动人的情致和纯真明朗的韵味。
从安史之乱直到宋室南渡,江南地区迅速发展,江南文化于此发生质的起飞,在中华文化格局中开始占据主动。“吴中四士”张若虚的一首《春江花月夜》,以孤篇压倒全唐,为唐诗增添了一缕空明、清丽和深幽的意境。安史之乱之后,大量文士避难江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江南风物的浸润下,受古文运动牵制的音律精细、辞藻巧艳的齐梁诗风被再度模仿。一叶知秋,由此可见江南文化此时在文化之影响。至晚唐,从文化的概念上来使用“江南”,借以指代“风光秀美、民熙物阜”之地的说法已然约定俗成。比如晚唐韦蟾《送卢潘尚书之灵武》有云:“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
到了南宋,随着文化人才进一步集中江南,江南文化经历了又一次的发展,特别是在“花轻似梦、雨细如愁”的宋词的带动下,“文人艺术”发轫。意境情趣、一味妙悟、含蓄空灵成为江南文化美学的中心。造型极简、釉色纯净又内涵丰富的宋代瓷器集中体现了这一点。而最能集中体现“文人艺术”审美品格的则是“文人画”。文人画在南宋兴起,于元至鼎盛,是中国艺术史上罕见的珍宝。文人画画家如赵孟頫、元四家皆出身江南。梅兰竹石、山水花鸟成为文人画新的描摹对象,诗、文、画、印的配合也与晋唐人物画迥然。无论是浑厚全景的北宋山水,精巧工致的南宋山水,还是水墨压倒青山绿水的元山水,对于“虚实相生、意在言外”的意境追求在不断递进。
从明嘉靖到清乾隆,江南一地哲学、文学、艺术流派众多、波澜起伏。发达的江南经济,市民阶级的兴起,文化世家的大量出现、阳明心学的宣扬流变,使得江南文化更加贴近世俗人情,求“俗”成为文学与艺术共存的倾向。这突出表现在文化艺术的迅速商品化上。以刻书为例,清代私营坊刻取代官刻和家刻,占据绝对优势,仅苏州、南京坊刻所刻之书就占全国总量的7/10,为迎合读者的喜好,其所印之书又以戏曲、传奇、小说、诗词、杂书为主。这类市民文艺不再载道言志,而是充满了对人情世俗的玩味,对富贵荣华的钦慕,对男女情爱的企望以及对公案神怪的兴趣。从明万历至清康熙的150年间,是中国市民文化之代表“话本”创作的繁荣期,从四大古典名著的作者到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作者,大都出自江南,其他话本小说的作者亦多江南人士。在此背景下,明清的文人画作也不免沾染了江南繁华市井带来的世俗气息。“吴门四家”、清初的金陵八家、清中期的扬州八怪把世俗生活画推向高潮。清末之海上画派则表现了更为浓烈的市民文艺色彩。皆因审美在日常,明清时期的江南饮食文化、园林文化、曲艺等等都达到了各自在中华文化中的历史最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