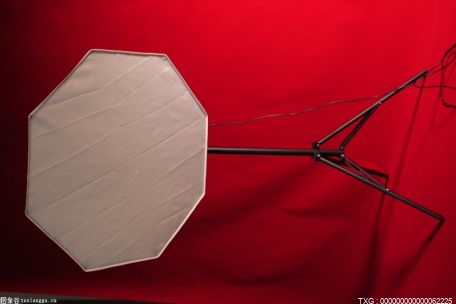无论是就内在意义而言,还是就概念本身而言,“现代性”都极为复杂。没有人能真真切切地给它下定义。作为概念的“现代性”既具有历史性和复杂性,又具有矛盾性和广延性,其中理路并非三言两语所能言说。尤其是在跨语际实践中,作为舶来品的“现代性”经过自西徂东的越界历程后如何完成中国本土的“在地”则更为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100年前鲁迅所谓“求新声于异邦”在21世纪的回响。所不同的是,“现代性”既涉及译介学和传播学问题,又指向哲学、美学和思想史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现代性”是如何在中国完成最初译介的?新时期“现代性”的译介浪潮是如何形成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性”的态度是怎样的?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审美现代性是如何终结的?

赵禹冰的《新时期美学译文中的“现代性”(1978-1992)》回答了这些问题。该书全面梳理20世纪以来的“现代性”译介问题,意在重返西方汉译的历史情境,从跨文化的视角考察其概念的本义,及其在离开原产地传播到中国文化场域中所遭遇的种种变形、调适、重组与再造的过程,进而探讨“现代性”概念在新时期中国美学理论建构过程中所起到的“起承转合”的关键作用。
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介绍了从新文化运动到“十七年”等“前”新时期的“现代性”译介;第二章以《文化:中国与世界》《走向未来》《美学译文丛书》《世界美术》等四部丛书为中心呈现出1980年代“现代性”及其存在方式;第三章强调的是1980年代学界围绕“现代性”产生的“新”困惑;第四章以波德莱尔和本雅明的译著为中心并旁及中国美学家的理论阐释,凸显出当时中国美学观念发生的转变;第五章以“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为背景着重介绍了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的“现代性”译介,最终指向“审美现代性”的终结。这些内容为读者深入了解“现代性”译介在中国的来路与归途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索引和理论依据。
首先,《新时期美学译文中的“现代性”(1978-1992)》资料丰富、内容翔实。一方面,作者全面爬梳了1980年代涉及“现代性”的几乎所有材料,其工作量可谓浩繁;另一方面,作者并不囿于材料的呈现和铺展,也极为注意对材料的分析,比如,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分析周氏兄弟所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进而说明为什么“二周”可以被看作是“现代性”译介的起点;再如,作者对波德莱尔“现代性”译介和问题的分析采用了文本细读的方法,几乎对相关文献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解读。这种以材料为中心并对之进行深入分析的方法奠定了该书的方法论基础。
其次,该书呈现了新时期“现代性”译介及相关问题的重要“风景”,揭橥了“现代性”尤其是审美现代性的发生过程。作为概念的“现代性”包含能指和所指双重指向,既存在其字面的形象意义,又存在更深层次的语言意义,进一步构成了问题的稠密与深度。因此作者不但关注了译介过程中的能指,而且也不忽视所指。比如作者在言及詹姆逊、哈贝马斯、利奥塔等人的译文时,非常重视从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层面总结“现代性”,关心的是所指。在此过程中,作者又勾连出了更为丰富的“现代性”问题,一是从历史和理论的源流处考察美学汉译的最初语境,并在此基础上讨论相关“现代性”概念的本土话语生成问题,二是从跨文化、跨语际的角度重审在“理论旅行”和“概念旅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异、重构、阐释等现象,进而强调概念如何完成在中国的“在地性”;三是以概念为中心勾连出了西方现代美学的重要内容,梳理了从尼采到利奥塔的西方“现代性”传统及其转向,称得上是西方美学现代性历史的中国书写。
再次,虽然这本著作是一部文学和美学著作,但是透过文本的肌理可以看到新时期的中国学术史。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学术存在一个与西方学术前沿问题双向互动的过程,经由几代学人不懈努力,已经呈现出与西方学术前沿问题同步化的倾向。在新时期早期,这种同步化的历程是由以“现代性”为中心的学术译介完成的,因此,该书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部别样的新时期学术史。陈来教授曾指出,在1980年代,“‘走向未来’的科学精神,‘文化:中国
与世界’的文化关怀,‘文化书院’的传统忧思,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年中国大陆文化讨论的几个侧面”,巧的是,这“几个层面”都涉及“现代性”问题。透过该书,作为思想和学术“行动元”的“现代性”概念一目了然。推而广之,作者经由“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想解决的是更为深广的问题,如其所言,“我们在新时期美学译文中有关‘现代性’的译介与讨论中,看到了有关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地域性与全球化、当下与未来、美学与社会实践、都市、环境、人口、市场经济、消费文化等一系列宏大理论和现实命题,这些都远远超出所谓‘美学’的学科范畴”,但作者也同时指出,这些问题都可以经由美学从最根本的层面给出自己的见解和回应,也足见美学现代性的重要性。
在该书的“余论”部分,作者指出,如福柯、阿多诺、布迪厄、德里达、维特根斯坦、大卫·哈维和阿瑟·丹托等思想家和理论家也应该进入到“现代性”译介研究的视野,因为“他们充满锐度和社会关切度的思想以及理论的斑驳与交互回响,混淆了‘现代性’的辨识度也构成了‘现代性’理论的丰富性”。这说明作者已经充分认识到新时期译文中的“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可延展性。如果以本书所讨论的截止时间1992年为新的历史起点,晚近30年来译文中的“现代性”译介及其所旁及的问题与方法将构建出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学术图景。对此,我们拭目以待。